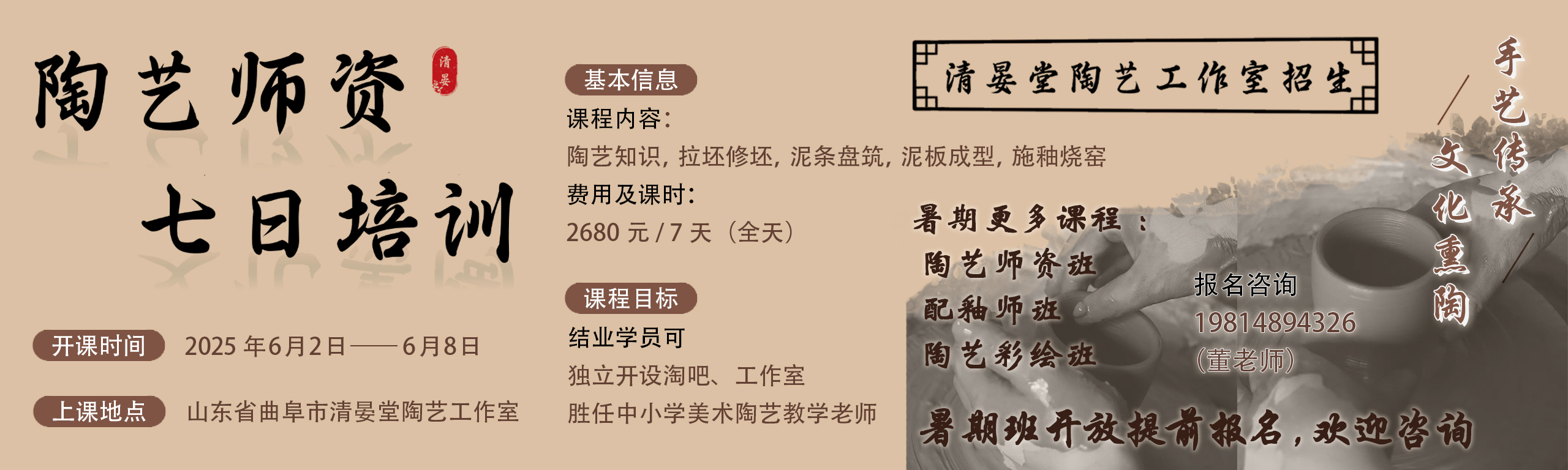来源:《孔子文化》第17期
作者:吴云
《儒行》同时见诸《礼记》和《孔子家语》,两者中的记载大同而小异,可以断定两者同出一源。关于《礼记》《孔子家语》真伪问题的争论到现在也还没有停止,两者中共有的这篇文献《儒行》在宋代以前被看成是反映了孔子所制定的儒者行为规范、准则。但到宋时,学者李观、程颐开始对《儒行》提出了怀疑,此后《儒行》真伪问题就一直没有统一的看法。

一、是否伪作的两种观点
历代学者持《儒行》为后世儒者假托孔子与鲁哀公问答之辞或漆雕氏之作观点的大致有宋代的李观、程颐、吕大临、卫是,元代的陈皓,清代的孙希旦,以及近人熊十力、任铭善、王梦鸥、郭沫若、杨天宇、吕友仁等。现将其主要观点罗列于下
程颐:“《儒行》之篇,此书全无义理,如后世游说之士所为夸大之说。观孔子平日语言,有如是者否?”吕大临:“此篇之说,有夸大胜人之气,少雍容深厚之风,窃意末世儒者将以自尊其教,谓孔子言之,殊可疑。”清人孙希旦:“此篇不类圣人气象,先儒多疑之。……盖战国时儒者见轻于世,故为孔子之学者托为此言,以重其道。其辞虽不粹, 然其正大刚毅之意,恐亦非荀卿以下之所能及也。”近代熊十力先生也推测该篇“其七十子后学当战国之衰而作乎”。郭沫若在《儒家八派的批判》中提出《儒行篇》“盛称儒者之刚毅特立”,也许是漆雕氏派的典籍。
纵观以上观点,认为《儒行》是伪作者基本上都认为其言“正大刚毅”,“学者果能践其言,亦不愧于为儒矣”,但“其辞不粹”,“有夸大胜人之气,少雍容深厚之意”,“孔子平日语言无如是者”,故而判断其非孔子之作。这种没有直接证据,从主观感受出发进行的判断,自然在说服力上是要打些折扣的,甚至是大打折扣,尤其不能使持《儒行》为孔子之作者信服“对同一文本, 不同的人读来,对文风、文气等感觉恐难一致 ,因此既可以作出肯定也可以作出否定。因此这种方法不足为据。”
持《儒行》所记为实事,成篇于春秋末战国前期者的依据主要如下:
(一)郑玄认为:“《儒行》之作,盖孔子自卫初反鲁时”;(二)没有直接证据证明其为伪作:(三)当时孔子及其弟子这一群体已被称为“儒”,而且当时人们混淆了“君子铺”与“小人儒”,亦即儒家”学派与传统之“儒”,所以孔子要对儒家之行进行阐发和解释,以回应人们对“儒”的话病:(四)准《论语》简约、《储行》铺张,文字上稍异趣”(章太炎:《<儒行>要旨》)。《儒行)中的思想与《论语》中所见的孔子思想是相合的,特别是末段数论“仁”,正是孔子“仁”学之旨。
二、 是否伪作之我见
综合比较两种观点,以及读《儒行》的一点感受,我觉得伪托之作的可能性更大,理由如下:
(一)《列子》《庄子》等一些文献里经常假托前人表达自己的思想,当然这种情况可能只是在列、庄的个案之中,但既然有这种情况的存在,就不能排除其他人没有这种做法。百家争鸣时儒家后学为己派辩护而假托孔子之言也不是没有可能。《缁衣》《坊记》等文献里大部分的“子曰”属于依托的可能性就非常大(汤一介、李中华先生主编《中国儒学史.先秦卷》)。
(二)我对发生这段故事的背景——哀公以儒为戏,时人以儒相诟病持怀疑态度。孔子在仕鲁前就“无论在学问上经验上都已达到很高的地步。教育成绩也很大,学生遍及四方,社会声誉很高。”(匡亚明:《孔子评传》)齐景公曾说要“以季、孟之间待之”;鲁国贵族孟僖子死前嘱托让其二子即后来的孟懿子和南宫敬叔投师孔子;鲁君资助孔子东观周礼等等。孔子仕鲁担任中都宰-年就“四方则之”,很快就升为小司空,后又由小司空升为大司寇。齐鲁夹谷会盟后,孔子更是声名大振。离鲁访问诸国期间,孔子虽然不见重用,“累累若丧家之犬”,但从卫灵公等对孔子的态度看来,孔子的社会声誉依然未减。当然名气大不代表别人就不会误会嘲笑他。但孔子后来回鲁是因为“冉求言于季孙曰:‘国有圣人而不能用,欲以求治,是犹却步而欲求及前人,不可得已。今孔子在卫,卫将用之。己有才而以资邻国,难以言智也,请以重币迎之。“季孙以告哀公,公从之。”既然是因为孔子“贤圣”而将其迎回来,又怎会刚见面就嘲笑他呢?再说,如果当时社会大部分人都因分不清“小人儒”和“君子儒”而诟病儒,那孔子又怎么会得到人们乃至贵族、君主的敬佩,子贡等辈又为什么放着好好的大道不走,却要背负世人的鄙视,在自己还不懂儒也有君子和小人之分的时候就投师个儒者呢? 就算为孔子的学识人格所折服(当然情况并不全是这样,很多人都是为了功利目的而从师孔子),他们走这条偏狭的儒者之路,世人也不会承认他们的能力,又怎么会有人要请孔子及他的这些弟子们出来做官呢?这似乎有点说不过去。再者,孔子群体“君子儒”是从“小人儒”中发展出来的吗?“从思想史研究的立场来看,其中的问题似很明显,试问,仅仅相礼的职业就能产生出孔子思想来吗?或者,仅仅从巫师和术士就能产生儒家思想吗?”(陈来:《说儒——古今原儒说及其研究反省》)儒的起源应与殷遗民有关,这个殷遗民应该是懂礼乐制度的遗民。礼乐制度本是治理社会国家的规范(“礼者,法之大分类之纲纪也”),但殷朝灭亡后,原先懂礼乐的贵族失去统治地位,不能再用其进行统治。新的周王朝也需要重新进行制度构建。史载周公制礼作乐,当然这不可能由周公一个人来完成的,“周因于殷礼”,于是原属于殷贵族的这些遗民所掌握的礼乐又有了被使用的空间,而新的周王朝也掌握了礼乐,所以应该将懂礼乐的人叫做儒(所以“以道术得民曰儒”)。有的儒能在位,以“为政教化”为目标,如周公,就是君子儒;而那些不得位,或者不以直接干政为目的而“友于兄弟,施于有政”(这种“施”可能不是主观目的而只是客观效果)甚至“堕落”到只是以相礼为职业的儒就是“小人儒”。因为子夏重视甚至有些只以“洒扫应对”等“小道”为满足,怕“致远恐泥”,所以孔子才教育他“女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就是说,“小人儒”殷遗民在商时亦是“君子儒”(当然当时也可能没有“儒”这名词),但可以基本肯定的是“儒”自产生或者到周时已不带贬义。并不是孔子从“小人儒”中发展出了“君子儒”。
这只是我对一段学术界未断之公案的一点看法,也许不足为据。从另一个角度说,还是要从孔子的“女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开始。首先假设人们当时还没冠孔子群体以儒,那孔子就是自认他们是儒,孔子为什么要选择一个“小人”群体的名字“儒”来命名自己,让别人产生困感、抹黑自己呢?如果当时孔子群体已被称为儒,人们又怎么会给这样一个社会声誉极高的贤人冠以具有讽刺意味的名字?而孔子及其弟子又怎么能接受呢?这不也有些说不通吗?
再退一步说,如果孔子是因社会上混淆了孔子群体“君子儒”与“小人儒”的区别,以“小人”之“儒”诟病孔子群体,而借着鲁哀公讽刺性的问话慷慨陈以“君子儒”之大德行,也不太说得过去。“人不知而不愠”,孔子的答话连用的16个“儒有”,气势压人,言辞间似有凛然不忿之色,不仅犯了愠的错误,而且也不符合孔子“事君尽礼以忠”的形象。连脾气火爆的子路面对荷蓧老人的无礼时都能做到“拱而立”,孔子怎么会失态到以“声色”夺君呢?表白自己,并戏剧性地以哀公说“终没吾世,不敢以儒为戏”为结尾,很像是儒家后学为反驳他派对已派的攻击,借孔子之口来树立已派威信的做法,这样也更能解释得通。
(三)将《儒行》中的思想与(论语)进行比较,有些地方也有些出人。当然,《论语》所载不是孔子的全部言行,不能仅以《论语》为标准来来判断《儒行》是否是孔子的思想言行。但是作为记载孔子及其弟子言行的著作,《论语》是了解和研究孔子迄今为止最可靠的材料,一直得到学者的重视。要判断《儒行》是否是孔子的思想言行,自然也不能撇开《论语》来考察,而且在没有更有力、更为大众所认可的材料出现前,我们肯定会首要以《论语》为参照。(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