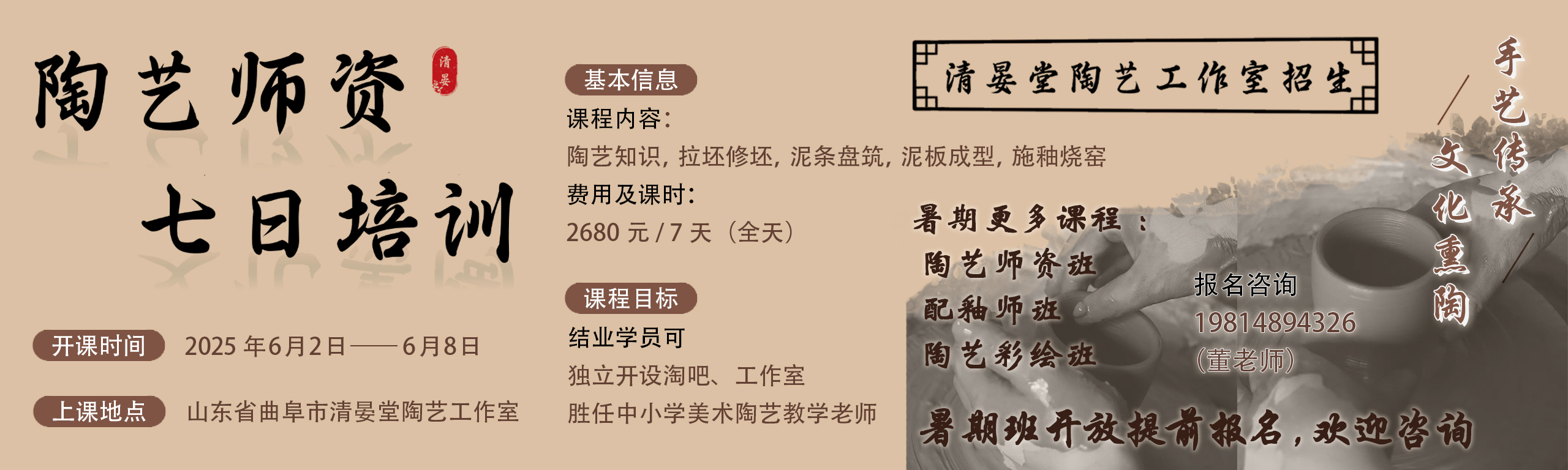来源:《孔子文化》第12期
作者:傅永聚、郑治文
(接上文)
秦汉大一统的新时代背景下,所谓“人主天下之仪表,主先臣随,主倡臣和”(《史记•太史公自序》)“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论语•八佾》),先秦儒家这套君臣“双向互动”的价值观念显然是大不合时了。儒家之旧学不行,新学未立,身处此种背景下的董仲舒面临着春秋之时与孔子相类的理论困境,孔子述而有作创立儒学,既承上古文化之旧局面,又开中古文化之新格局,实现了上古与中古的沟通衔接。或许正是鉴于孔子兴亡继绝、贯通古今的文化贡献,董仲舒继承和发挥了孔子述而有作的文化精神。深刻意识到先秦儒家政治理论不合时宜的董仲舒并未尽弃其学,全盘否定,而是辩证的审视了先秦儒家一长一短的双重理论品格,在此基础上开始了其新儒学的建构。一方面,他继承和发展了先秦儒家政治理论中“序君臣父子之礼,列夫妇长幼之别”《史记•太史公自序》)的合理精神,此谓“扬其长”、“返其本”;另一方面,有鉴于先秦儒家政治理论“迂阔”之短,他又注入了合乎“大大一统”时代背景的法家化、政治化的新内涵使儒学可以致用,此谓“避其短”、“开其新”。述而有作,扬长避短、返本开新正是董仲舒构创新政治学说的内在理路。述以扬其长,作以避其短,一返本一开新,董仲舒终于建构了合乎时代需要的新型儒家政治哲学体系。

述而有作、扬长避短、返本开新的文化精神在董仲舒新政治儒学体系中多有体现,并集中表现于“三纲五常”思想中。董仲舒博大精深之学说体系,一言以蔽之,曰“屈民而伸君,屈君而伸天”。(《春秋繁露•玉杯》)就其整个思想体系来说,“屈民而伸君”的“尊君”论主要是对先秦儒家政治理论“不切实际”的一种大纠正,为此他以儒为宗、博采众家之长给儒学注人了新内涵,“儒学与阴阳、道、法、名诸家思想相结合,这种结合导致的直接后果,就是使儒学更趋于实用。”(刘学智:《三纲五常的历史地位及其作用重估》,《孔子研究》,2011年第3期,第19页。)这主要是“开新”,是“作而避其短”;当然也是对先秦儒家“序君臣父子之礼”的拓展,故也可算是“返本”,是“述而扬其长”。其“屈君而伸天”的“抑君”论,主要是对先秦儒家“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论语•八佾》的继承,同时又包含了对君臣“双向互动”关系的超越。就“三纲”思想来说,与先秦儒家“序君臣父子之礼,列夫妇长幼之别”(《史记•太史公自序》)恐怕还是大相径庭的,“孔子从维护周礼的立场,提出了保持君臣、父子上下尊卑秩序的重要性,强调‘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这对三纲观念的孕育无疑有某种催化的作用。但是从《论语》来看,孔子并不认为君臣之间必须是单方面的绝对服从关系,而主张‘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这里,君臣之间还只是体现着双向互动的关系。关于父子关系,主要体现在他说的‘孝’道中,孔子的孝主要体现在‘敬生事、死葬终祭’等方面,同时又主张父子互隐,这些都似与‘父为子纲’不搭界。《论语》中没有明确讲到夫妻关系,更谈不到夫妻的尊卑秩序问题。”(刘学智:《三纲五常的历史地位及其作用重估》,《孔子研究》,2011年第3期第20页。)到汉代时,为使儒家政治理论“合时”、“实用”,董仲舒注人了新内涵后这种情况就发生了“大转型”。他说:“君臣、父子、夫妇之义,皆取诸阴阳之道。君为阳,臣为阴;父为阳,子为阴;夫为阳,妻为阴。”(《春秋繁露•基义》)这里董子虽为直接提及“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然若按其“阳尊阴卑”论来理解,“三纲”之义不言自明了。所以由孔子“君臣父子”之说到董子“王道三纲”之义的“大转型”则明确彰显了董学创立的“作而避短”精神。至于“五常”,先秦儒者那里似未直接提及,然“仁”、“礼”是孔学之核心,“智”、“信”多见于《论语》,“义”在孟子那里多有发挥。“夫仁、谊(义)、礼、知(智)、信五常之道,王者所当修饬也。”(《汉书•董仲舒传》)董子虽明确将“五常”规定为“仁、义、礼、智、信”,然“五常”的“发明权”似应归功于孔孟,只是到董子这里又辅于五行之说加以证明。所以“五常”之说由孔子智、仁、勇“三达德”,孟子仁、义、礼、智“四端”至董子“五常”之道是董学创立的“述而扬长”之精神的明确表达。总的说来,“屈民而伸君”、“三纲”主要是“开新”,“屈君而伸天”、“五常”则主要是“返本”,述中有作,作不离述,相辅相成,并行不悖。
述而有作是孔子创立儒学的内在理路,亦是董学建构之基本精神。孔子述“礼”作“仁”创立儒学,借助于仁,中国传统文化顺利地实现了由上古向中古的转折;借助于仁,孔子之前数千年和孔子之后数千年的文化血脉得以沟通连接,而没有中绝断裂。柳诒征先生言“孔子者,中国文化之中心也。无孔子则无中国文化。自孔子以前数千年之文化,赖孔子而传;自孔子以后数千年之文化,赖孔子而开。即使自今以后,吾国国民同化于世界各国之新文化,然过去时代之与孔子之关系,要为历史不可磨灭之事实。”(柳治征:《中国文化史》(上),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263页。)斯之谓也。秦汉大一统的新时代背景下、儒家“述而有作”的理论品格在董仲舒那里再次得到了完美诠释,他既承先秦儒家政治思想之大成,又纳人了合乎时代精神的新内涵,由此建构了儒家博大精深的政治哲学体系。孔子还而有作,“可以说,他(孔子)的思想学说是‘集’了中国上古以来文化之‘大成’。故孟子云:‘孔子之谓集大成’,正因为孔子的集大成,他才能有那样巨大的思想潜力影响了中国历史文化又两千多年。”(韩星:《全球化背景下的儒学与中国文化整合》,《东方论坛》,2006年第1期。)以此观之,董仲舒亦是此等人;以此观之,孔子、董子之后儒学的新开展亦是“述而有作”之精神的继续。宋明诸儒本于汉唐经学之成就,又“援引佛道”,三教调合而有新儒学;现代新儒学则是古今对接、中西合璧的产物,其返本开新、“接着讲”的文化纲领实乃儒家一以贯之的述作精神的现代演绎。
可见,儒家每一次新的飞跃,无不是对其“述而有作”之精神演绎和发挥的结果。如果说儒家之成功在于述而有作,那么述而有作之成功则在于它正确揭示了人类文化发展的普遍规律:文化之保守与创新是文化发展的双重张力,两者相反相成,对立统一,不断推动文化前行。文化保守就是文化之民族性继承;文化创新则是文化之时代性转换,文化之民族性继承必以“时代性”为指引;文化之时代性转换必以“民族性”为依托。从民族文化学的意义上来说,保守不能轻易否定。因为它体现了一个民族文化性质稳定性的一面。创新只能在已有基础之上进行。保守与创新是相辅相成的对立统一体。恩格斯所谓“它(学说或思想)必须首先从已有的思想材料出发,虽然它的根源深藏在经济的事实中。”说的就是这个道理。现代化建设如火如荼展开的今天,“传统与现代”正是我们面临的时代性课题,“述而有作”恰是孔子、董子等儒家圣哲泽及吾人的精神财富。(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