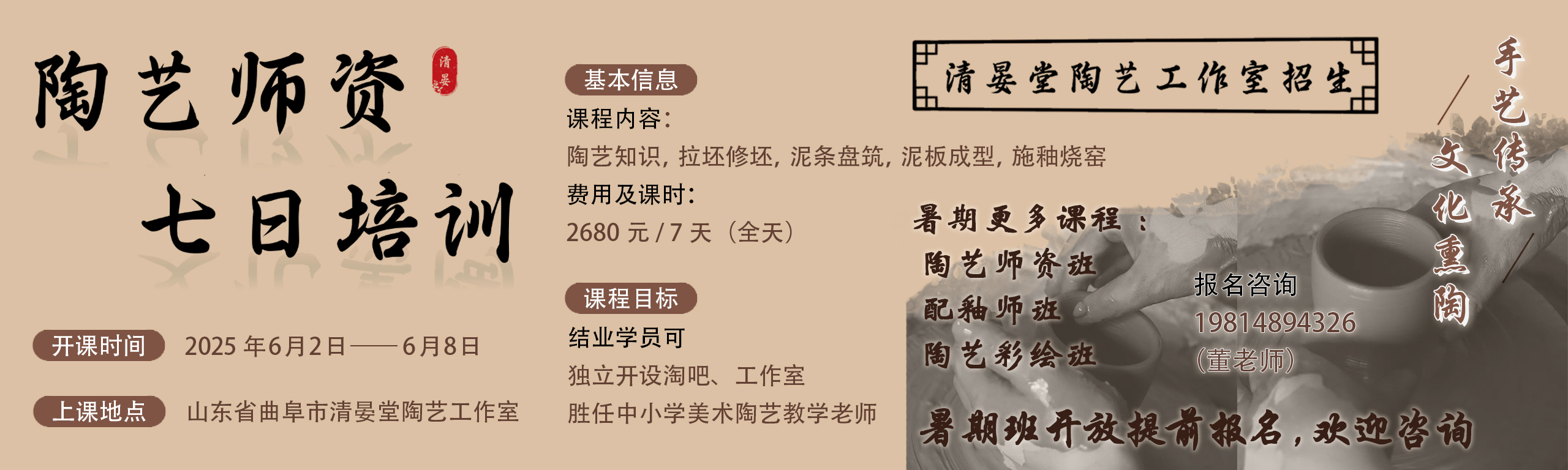来源:《孔子文化》第14期
作者:黄怀信
七、“文”和“行”

《论语•述而》篇载:“子以四教:文、行、忠、信。”专门以之教,说明四者在孔子心中占重要位置。这里的“文”,指文献和文化知识。他所说的“(弟子)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学而》)、“君子博学于文”(《雍也》)、“文,莫吾犹人也”(《(述而》)、“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子罕》),及颜渊所说的“夫子循循然善诱人,博我以文,约我以礼”(《子罕》),其“文”字皆同于此。可见他主张学“文”。而“文”,显然不同于武,所以“文”又与“武”相对。他主张“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季氏》),表现了他对“文”德的重视。
学“文”,自然有益于文化及社会文明的进步。所以,其学“文”的思想是进步的。
“文”,又指文明、有文采,接近其本义。有了文化,自然就有文采。孔子说:“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八佾》)并赞叹“尧之为君也”。“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焕乎其有文章”(《泰伯》),又表现了他对文化及文明的向往。可见孔子主张学“文”,最终是为了社会文明的进步。
四教之“行”,指行事、做事,乃至行身。以往或理解为品行、德行,明显是错误的,因为若指品行、德行,则与“忠”、“信”重复。且《论语》中“行”字出现八十二次,指品行者只有一处,即《先进》篇“从我于陈蔡者”章所附“德行: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之“德行”。而此语显然出《论语》编者之口,与孔子之“行”非为一事。所以“文、行、忠、信”之“行”,必不能以品行或德行释之。
孔子教弟子“行”,自然是教他们做事和行身的原则与方法。比如他说“放于利而行,多怨(《里仁》),意思就是做事不能以追逐利益为目的;说“我(旧脱)三人行,必得(或误‘有’)我师焉”(《述而》),就是教人做事要多听他人意见,不要自以为是;言“文,莫吾犹人也;躬行君子,则吾未之有得”(《述而》),就是劝人多“行”、多实践。他主张“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里仁》),提倡“先行,其言从之”(《为政》),要求“君子耻其言之(旧曰误“而”)过其行”(《宪问)》)、“言必信,行必果”(《子路》),认为“言寡尤,行寡悔,禄(福)在其中矣”(《为政》)等 等,说明他对“行”的重视。
关于行身,他也有很多具体的主张与方法。
比如樊迟问“行”,他说:“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虽之夷狄,不可弃也。”(《子路》)子张问“行”,他说:“言忠信,行笃敬,虽蛮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笃敬,虽州里行乎哉?立,则见其参于前也;在舆,则见其倚于衡也,夫然后行。”(《卫灵公》)皆是讲行身的方法。
由此可见,讲究“行”也是孔子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当然,“行”有一个原则,就是“中庸”。
八、“中庸”
孔子说:“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雍也》)可见他认为“中庸”是最好的“德”。“中庸”是什么?前人亦有多种不同的解释,我们不去引述。这里,先从字义和文法来作分析:
《说文解字》“中”字训“内也”,为引申义。根据古文字的写法,“中”本义应是居中的意思。那么,引申之,恰到好处、合乎标准,自然也可以谓之“中”。所以段玉裁《说文解字注》云:“中者,别于外之辞也,别于偏之辞也,亦合宜之词也。”无疑是正确的说法。合宜,就是恰到好处、合乎标准。所以,从文字的角度讲,“中庸”的“中”有表示恰到好处、合乎标准的可能。而根据孔子自己“过犹不及”的说法,“中”应当就是这个意思。
“庸”,《说文》训“用也。”而根据古文字的写法,“庸”象悬挂着的镛。所以,“庸”应是“镛”的本字。当然,“用”字本来也是“镛”的象形,后来才假借为使用的用。可见“庸”、“用”本属同字。正因为“庸”、“用”本属同字,所以周代文献中“庸”皆与“用”同义。“庸”还有“常”义,即由“常自用”(《尚书》孔传解“庸”语)引申而来。然而“中常”显不成词,所以,“中庸”之“庸”只能当用来讲,“中庸”就是“中用”,“庸”应该念去声。
“中庸(用)”是什么意思?首先,根据古汉语语法,“中庸(用)”只能有两种解释:一、中之用;二、用中。而根据“中庸(用)之为德也”的说法,“中庸(用)”是一种“德”,而“中”与“用”显然又不属于道德,所以,这里的“德”只能是指德行。既然是一种德行,那么“中用”就只能是指用中,而不能是中之用。所以,前人解为“用中”一说,应该是正确的。说“中用”而不说“用中”,根据古人的语言习惯,无非是为了强调“中”。当然,这种语言习惯出现比较早,而且根据孔子“民鲜久矣”的说法,“中庸(用)”应是一个比较古老的词汇,而不是孔子自己所创造。所以,我们不必怀疑“中庸(用)”可以当“用中”讲。
“用中”是什么意思?我们说,“用中”,就是运用“中”;运用“中”,就是凡事皆执其“中”;执其“中”,就是把握事物的标准,凡事皆做到恰到好处、合乎其宜、无有过与不及。《论语•尧曰》篇记尧的话说“允执其中”,《尚书•大禹谟》记舜的话讲“允执厥中”,无疑就是这个意思。显然,执“中”,是最好的行事方法,所以孔子称它为“至德”。而凡事做到“允执厥中”、恰到好处、合乎标准、无过无不及并非易事,因为你首先得了解它的“中”、知道它的标准。而民之所以“鲜久矣”,就是因为他们不能正确认识和掌握“中”,所以做事也就不能合乎“中”。
怎样知“中”?《逸周书•度训》篇云:“度小大以(立)正,权轻重以(立)极,明本末以立中。”就是说要知“中”,必须先明本末。本末,即两端。所以孔子自己也说“舜……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中庸》)引“子曰”语,见《礼记•中庸》)。可见知“中”须要执两端。执两端,才能知道其“中”之所在;知“中”之所在,才能有“中”可用。所以,知中是用中的前提。可见“中庸(用)”之不易。
正因为“中庸(用)”为至德,而又不易做到,所以孔子教弟子学“中庸(用)”。《中说》卷四载:“游仲尼之门,未有不治中者也。”“治中”,即讲究中庸。可见孔子确实讲“中”。
做事若能恰到好处、合乎其宜、无有过与不及,自然也会中礼,所以“中”往往又与“礼”联系在一起。
由此可见,“中庸”本是处理事情和行事的方法,在孔子那里,更被作为做人和行事的原则。所以当子贡问“师与商也孰贤”的时候,他答曰“师也过,商也不及……过犹不及”。(《先进》)
需要强调的是,“中庸”绝不是折衷。折衷是在任意两者之间取其中,而“中庸”则是在“本”“末”之间取其中。
另外还需指出,以往将《论语》中的“中行”也理解为中庸,实际也是不对的。因为《论语》的原文是:“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子路》)“中行”,是指行为、动作的频率适中,不紧不慢,所以与狂狷对举。狂,指疯狂;狷,指狷急。疯狂,故有进取心;狷急,故有所不为。疯狂、狷急,皆胜于懒散不为,故可“与之”。行为、动作的频率适中可以谓之“中”,但并不是“中庸”,因为它只是人的行为习惯,而不是刻意地“用”。(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