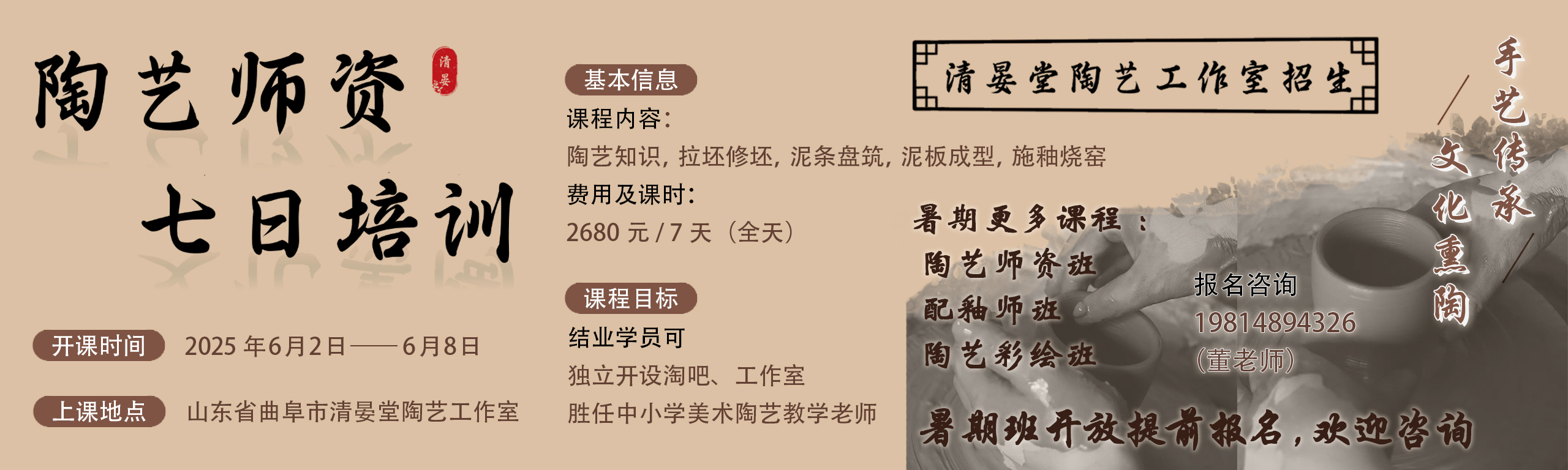来源:《春风》1996年第1期
作者:范尔进
桑拿着肥皂盒走进水房。

上午的课很好,很有启发,外面的阳光投射进来,整个水房明晃晃的,白瓷砖墙上移摇着自己的影子,桑打量着,同时搓动着双手,感到舒心极了。瞥见一人站在另一侧洗东西,长长的一根黑辫子到腰际,觉得有些像本系同学迪,回望了一下:“迪,有开水吧?”“有,早上刚打的,去倒吧。”软绵绵的南方口音,让人很亲切,很舒服,也很容易让人产生站在一旁听说话的念头。到了这学校读书后,桑已学会凭气息辨知南方北方女人。
桑推开迪宿舍门。
房里充满了炖牛肉的热气,正前的小瓷盆里正翻腾着酱油色泡沫,小电炉有些喘不过气地被压着。搬进这座宿舍楼不久,只要一到吃饭时间,楼道内安装的电压超负荷警报器就要开始不停地鸣叫——断闸——被开启;鸣叫——跳闸——被开启,循环往复,因此有自觉性的同学,尤其是桑她们系的同学是不愿白找麻烦的,情愿多跑些路,多花些钱到饭堂买着吃,哪怕吃的不可口。一是由于她们年龄大,自认学识和修养远高出其他系;二是整日忙于读书、写作、出成绩,没时间顾吃喝。桑倒好水对迪打趣说:“还补哪,都啥样了。”刚才在水房里见到迪的背影时,就有吹起来的感觉。迪没说话,嘴启合了两下又停在了空中。一般当有什么话想说而又不知如何开口时迪的嘴就是这样。“怎么又坠入情网不能自拔,啦?”桑对着水杯叶着气不屑地说。迪的脸色不好,眼袋明显下垂,早先由于生孩子而留下的褐色斑似乎比以往明显,尤其是那两只早先总是扑闪闪地动情地显示着低于实际年龄的眼睛,今日是蔫了。桑知道迪一定是碰到难处,受到了煎熬。迪站在原处,叹了口气,,没说话。桑也不便再问,想退回去,又怕自责不关心人,于是也叹了口气,“这世道谁都被愁困扰啊!啊——”就此转身。“桑,我怀孕了。”迪的声音无力地飘过来,既遥远,又清晰。桑同声音一样缓身停住:什么?怀孕?桑似信非信地有些不可思议:学校条例里规定学员是不允许结婚、离婚和怀孕的,更何况她不是已有一个孩子了吗?。桑望着迪的嘴,“真的。”迪说。瞧着她,桑又一次感受到了表情的力量。桑替她愁了起来:“几个月了?还不快去做流产。”“明年六月生,正好那时我们实习。”啊?要孩子!桑小吃一惊:“你定下想要孩子啦?”迪用劲地点了两下头,坚决般地慎重,似乎把勇气和决心统统凝聚在了里面,但中间似乎又夹杂着无奈的成份,好像这无奈饱含着忍受和服从。桑似乎一下子感受到许多,但又说不清。是和谁的孩子?桑想确证,但又觉问话多余。想劝她,给她摆出些不利,觉得也多余。桑感到有些不便直视迪的眼睛了。对着杯中水说:“你再多考虑考虑,和家人商量商量。”桑头一次发现杯中水莹光闪闪,不知是有害物质呢?还是对身体有利的元素。桑退出了房门。
桑端着饭盒走在去食堂的路上。
“是和谁的孩子?”桑推测着时间。尽管刚才桑没问,迪也没说,但这对桑和迪来说似乎是不言而喻的问题。迪不说怕是认为桑明白得很,而桑呢?她有点不敢相信。理由太多了:于想象中的违背常理的事情轻易不敢和现实兑现;更何况小说中的素材于生活中县少至甚少。还有,做纵观历史横察人性工作的人有必要把自己也投身其中作为标本进行剖析吗?有为之投入的必要和价值吗?推测结果后,桑自言道:“糊涂了,糊涂了。”似乎是迪糊涂了,又是迪把桑弄糊涂了。拐了路口,见远处一俊男拎着一叠饭盒迎面而来。他非常流畅地走近。衣服得体,意气勃发,很有点春风得意的劲头。无论他的表情如何平稳,桑似乎感到与以往不太一样:气有些外溢,有点过了。“数你打饭不积极,”好听的男中音和桑打着招呼。桑有些笑不出地挤出点笑:“迪已在等你了。”“又不是你等我,急啥。”桑没在意他的话,想是迪合适他呢,还是他的妻子合适他呢?桑比较了一下还是迅速明确:迪更合适!可是,是他合适迪呢?还是更合适他妻子?桑想:还是他适合他妻子。桑曾经见过一次他妻子,那是一位黑黑瘦瘦有些厉害的北方姑娘,桑当时想如果知道自己的丈夫找了情人能咋样呢?凭她脸上的雀斑就知道轻饶不了。但那些黑密的小雀斑又能将性格中本应自然坦露出的东西遮去多少,剩下的就不好说了。前面一颗大榕树,稳稳当当结结实实地站着,张开丰满的枝叶全方位地占领着应属于他的空间,力所能及地布满着羽翼般的花,绛红色,煞是好看。来往的同学不由地都想踮脚够下一束,拿在手中摆弄着。其实他们也未必真喜欢,真正喜欢花的人是不忍心摘花的。桑想着。
桑站在窗口打饭。
明亮的大饭厅,由许多铺着白色布的桌子和数不清的靠背椅组合而成。两排对列的大玻璃窗齐唰唰敞开,使房内的热气及时冒出,给外面的轻薄的含氧高的气体腾出地方。内外交换。人体需要如此,动物植物体亦如此,还有更多的包括人类知道的和不了解的物体还是如此,或许家庭做为一个实体也要不停地进行此种不易让人知晓的运动。桑看着被扭曲了但基本保持原形的铝盆,沉重的大头铁勺很不客气地压着边缘,里面的菜被颜色和厨师的劳动搅得已面目全非,找不出一点原形。桑没了味口,不知晓的东西对懦弱的人来说是有距离的。回身望了一下满饭堂围在一起的人,除了感受到同学们惯有的吃、说热烈外,桑接受到一眼光,那是桑自己也说不清的复杂眼光,桑随即拿着饭盆走出了饭堂。她知道那眼光会长线似的拽着后襟,直到视觉转弯处。桑讨厌任何已婚男人眼里流露出的有关自己的用语言表述不便的神情,她把这神情常作为一种有害物质或瘟疫加以拒绝和逃避,唯恐这东西由单细胞发展,不断扩散繁殖成一种有形的有生命的怪物攀附在身上,纠缠你,让你不能自己,失去自己的呼吸,失去自己心爱的脾气,失去原先的感受生命方式,直到最后窒息在另一个自己都不认识的躯体里。这躯体发出的语言信号陌生,做出的行为不可思议,犹如梦中被魔鬼勾去魂的自己在空中漂浮,脚下没有土地。对桑来说没有灵魂等于没有生命体,活着没有任何价值意义,还不如来世重新投胎,以自己属于自己的形式活给自己。桑刚来校不久,见到一位在事业上颇有建树的大自己许多的已婚男人,他们对视的第一眼,桑就感到熟悉.感到是早已安排好如约而至的相逢。桑在感知着自己要成为第三者并且不得不为之的时候,桑听到一种声音,由远而近而清晰。那是一种由神奇的植物发出的声音。桑开始听不懂,于是就贴在上面用皮肤触知,谁知植物的花瓣现出了人形,是桑正倾心的男人。当桑好生奇怪时,男人的脸面开始消瘦——消瘦,直至成了可怕的人面相。打这之后,桑见到他总是好生地盯着他看,看他如何动用表情,如何使用语言技巧,如何身体力行地使用动作。桑试图探测语言、表情的联合功能,试图搞清思想指挥语言和语言表述思想之间的关系;并思考表情、语言的背后是什么呢?桑最终也没有得到实践可以检验的真理。直到现在桑还纳闷:因为拒绝约会会致使很痛苦的他怎么没有痛苦的症状呢?
桑纳闷的事情越来越多。在带着疑问的时间里,树叶由绿渐黄,漂亮的羽翼似的芙蓉花也成了抽缩的问号似的弯勾状勉强地攀附在枝上,宿舍楼道里嘀嘀嘀的警报声更频繁地闹着,似乎已没有了停息的时候,食堂里的那两排大窗户已封闭上,因开饭时的热气没有更好的地方散发,饭桌四周同学们的吃、说显得更热烈、气氛更融治,表情在雾中也显得湿润而含蓄,语言因此也变得随意、亲切。桑觉得食堂由此单纯了,你、我、他没有了区分,甚至无法鉴别了。
秋日的晨光把银杏叶的金黄附上了流彩。同样流动在金黄的地上,桑同迪在走着:
迪说:说好了等我的,怎么又不在呢?
桑说:招待所条件还好吧?
迪说:过些日子该生了,心里有些不安。
桑说:学校食堂里的饭还是糟。
迪又说:他会不会因学校临时有事出去了?桑不想问迪家里的婚离的如何,也不想关心桑何时能和个情人结婚。桑只是看迪踌躇地走在流彩上,看迪头上的黄叶子天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