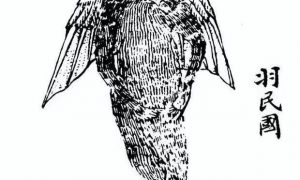作者:马士远
涵咏上文,玩味其文理词气,不难看出子墨子只言《周书》、《商书》、《夏书》有鬼,并未继续上推,而是以“故”字为转折,紧接其后对其上所说夏、商、周之《书》有鬼神之事进行语义概括,其概括范围就只能为“《夏书》,其次商周之《书》”,不可能包括《虞书》,这是就上而言。就下而言,若按郭说“尚书”指《虞书》,则《虞书》、《夏书》、《商书》、《周书》属于并列关系,《夏书》、《商书》《周书》“语数鬼神之有”,子墨子已在上文举例明言,却并未言《虞书》鬼神之有,又怎能说《虞书》也“语数鬼神之有”呢?显而易见,郭先生认为“《墨子·明鬼下》’尚书夏书,其次商周之书’这段文字以上已经不止一次地将虞、夏、商、周并举,此处不当只言《夏书》、《商书》、《周书》,而略去《虞书》”的观点是不符合《墨子》文本事实的,仍有商榷的余地的。
最后来看其第三条理由。马融所说“上古有虞氏之《书》,故曰《尚书》”,其意并不是将《尚书》指认为《虞书》。在先秦人观念里,商、周两代去古未远,并不属于“上古”,只有夏代及其之前的的时代才够资格被称为“尚”,而在先秦人的观念中,虞、夏之间的界线是很难明确区分的,这种视“尚”为虞夏时代的观点一直至西汉初年才被转换。马融是东汉时期的大学者,其学犹精于古文,在其学说中,直接继承先秦时期的观点,而有别于汉代经学界的新观点,是完全有可能的事。
陈梦家先生早就指出《墨子》所言“尚书”是指《夏书》。他说:“《尚书序》孔疏引马融日:’上古有虞氏之书故曰《尚书》’,至汉并商、周书亦曰《尚书》。《墨子》的’先王之书’亦即尚书之意。”由此亦可以看出,陈梦家先生亦主张《虞书》与《夏书》是一回事。其说确有道理,在《墨子》时代,在墨家学者眼中,只有《夏书》可被视作上古之书,商、周之《书》并未被视作上古之书。
由以上分析来看,郭沂认为《墨子·明鬼下》“故尚书夏书,其次商周之书”的“尚书”指《虞书》的观点是难以让人信服的,不过,他认为“尚书”在先秦时期“是普通名词,非专用名词”“凡‘上古之书’皆可被称为’尚书’”的观点却是有其独到之处的,只不过对“上古”时代的界定还需进一步考解。
按一个角度来看,此处“尚书”也不可能是专有名词《尚书》。在《墨子》一书称引古籍中,称引《书》者最多,据笔者统计多达42条,其称引的方式有“先王之书”加篇名者凡13 次,直接称引名者凡 15 次,称《夏书》之后加篇者名1次,称说《夏书》、《殷书》、《商书》、《周书》、夏商之《书》者凡6条,还有称《传》曰、“先王之言”“先王之誓”等不同情况者凡7条。如果把这些称引分类无论先王之《书》、先王之言、先王之誓,还是《夏书》、《商书》、《殷书》、《周书》,都可视为和《书》,这是一类,还有一类就是直接称篇名,不可能破例直接称《尚书》1次。
据以上分析可知,在《墨子》一书中,“尚书”与“书”各有所指,“尚书”是指“上古之书”。在此处专指《夏书》,不可能《两书》与《书》并称同指六经意义中的《尚书》。
笔者认为:“尚书”在这里与《夏书》、商周之《书》之间不是同级并列关系,亦不属于上下级的包举关系,此处“尚书”仅是对《夏书》而言的,“尚书”与《夏书》是同义复指关系。“故尚书夏书,其次商周之书,语数鬼神之有,岂可疑哉!”其意思是说:上古之书《夏书》,还有《商书》、《周书》多有鬼神存在的记载,怎么能怀疑呢!
二、出土帛书《易传·要》篇“尚书”意旨探微
由马王堆3号汉墓出土的随葬木牍可知,该墓下葬于汉文帝前元12年,即公元前168年,至于《要》篇的抄写时间、祖本的写成时间学界意见不一,日本学者池田知久以传统的《老子》一书的晚出和“‘尚书’在先秦时代单称为’书’,只是到西汉初期才开始由伏生或其弟子欧阳氏使用这一名称”的理出,认定《要》篇成书的年代“是在从西汉初期的高祖到吕后,即公元前206年一前180年之间”。从战国郭店楚简出土的文献有《老子》一书来看,其说肯定是不能成立的;而且,池田先生在考证之前已经默认了帛书《易传·要》篇中的“尚书”为经学意义上的六经之一的《尚书》,依此推断《要》篇的生成年代,事实上已陷入循环论证的怪圈,故其有关帛书《要》篇“尚书”二字的见解不可信从。
王葆玹先生则认为《要》篇关于《尚书》的议论,恰与焚书的事件相关,“《要》之原文不论是’勿”还是’口’,原义都是说《尚书》的多数篇章已不存在”,并据此“判断《尚书》一名的产生时间,应在秦始皇三十四年(西元前213年)以后,西汉以前”,“《要》之撰写又应晚于《尚书》之名的出现,当是撰于秦二世至子婴的时期。”目前古文字学界对“尚书多”之后的那个字为何字还没有定说,以对其错测性地释读为据而判断其义为“《尚书》的多数篇章已不存在”,与焚书事件有关,进而考定《要》篇的生成年代,只能算–家之说,但还不能看作定论。
廖名春先生以马王堆3号墓所出帛书的错简较多、《要》篇书写形制、篇题及其所记字数为依据,考证《要》篇当为抄本无疑,抄写时间当在下葬之前,《要》篇“应有更早的篆书竹简本存在,而《要》的写成,当又在更早。《要》篇系摘录性质,其材料来源应较其成书更早。考虑到秦始皇公元前213年据李斯议制定了《挟书令》,而该令直到汉惠帝四年(前191)才得以废除。考古发掘表明,迄今在《挟书令》施行时期以内的墓葬,所出书籍均未超出此令的规定。所以,帛书《要》篇的记载不可能出自汉初,也不可能出自短短十五年的秦代,应该会早到战国。”并且他又对帛书《易传》其它篇的写成时间进行考证后认为:“写成最晚的当属《缪和》《昭力》,但它们所记史事最晚也为战国初期之事。而且《缪和》所载,往往比《吕氏春秋》《韩非子》所记更为详实,如果它不是在《吕氏春秋》、《韩非子》之前写成的话,是很难做到的。”其意显然认为《要》的写成当早于《缪和》《昭力》。廖先生据此又推论出是孔子始称说《尚书》的,他说:“《尚书》之称当起于先秦,如郑玄《尚书赞》即云:’孔子乃尊而命之曰《尚书》。’其说人虽不信,但与帛书《要》篇记载孔子称’尚书’说可印证”。可见其意是将《尚书》之称定为孔子。
声明:该文观点仅代表作者本人,国学百科网系信息发布平台,仅提供信息存储空间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