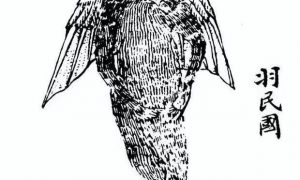作者:钱 爽 张耀南
如若我们仔细深究,便会发现这种西约(西洋政治哲学史上之“约”)与墨约还有着另一层截然不同的区别,那就是西约自始至终都缺乏互系性特征:
“神约”看似是由神与人(君与民)共立之约,其参与主体同墨约一样三极兼备,但是西洋“神约”中的神是外在于世界且有着绝对之权威与能量者,人只能对其信仰与虔服,无法与其进行真正的交互。只有人对神信仰,才有神对人的庇佑,反之则将招致灾祸。因而在“神约”中,神永远居于至高至尊的地位,这是居下的人永远无法改变的预设前提,人在神的面前永远只能处于服从地位。这样的神是与墨家所言之“天”迥异的,墨家所言之“天”是“兼而爱”“兼而利”“兼而有”“兼而食”的,它“行广而无私”、“施厚而不德”、“明文而不衰”,绝不会因为人不认同信仰之约便取消对人的庇佑而降灾于人;同时,人亦可以通过德与礼的“敬事天”来约“天”,使人“得福”而无祸。在“天”看来,对人的唯一要求就是以道德伦理爱人利人而仁之,信仰并非是实现“天”与人交互的唯一途径(况且德与礼的“敬事”亦与信仰有很大的不同)。倘若真正对神信仰了,事实上也就没有所谓的交互了,因为信仰看似是一种互动行为,实辄是神对人的一种有形的“伪交互性的单向束缚”而已。所以,西约之“神约”并不存在真正的互系性表现。
“政约”亦看似是人世间的君与民互立之约,君与民表面上实现了互动,但在著者看来“政约”却已经开始将主动权向民转移且逐渐集中于民了,君或许只是因为民为了维持既定的中世纪封建制度或与教权相斗争才具有其存在价值。所以,“政约”看起来通过彼此的权利与义务界定了君与民之间的关系,然而真正从中孕育而出的却是主权在民的思想。所以,只能勉强说西约之“政约”有了君与民交互或互动的端倪,但本质上还是只有民约君的表现,而君约民则弱了许多。可是,这种鲜有的中世纪“政约”互系性的浅层表现却在近世“社约”中彻底消失并完全转为民在“约”中的主导及主动地位了。
以霍布斯为肇始的社会契约论被有些学者誉为是西约层面的“哥白尼式的革命”,这是因为“社约”否定了古希腊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所主张的城邦共同体主义,转而进入了反传统的个人主义,从而使古希腊的这种“父权主义和自然主义的预设结构”走向了个人主义的社会契约论。实际上,这从一个极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即由民完全地服务与受约走向了民绝对地约君。
西约自古希腊时起直至近世社会契约论乃至当代新契约论,虽然不断地实现了其内部的前后超越,但始终无法实现真正的互系性。与先秦墨家互系性通约论相比,著者认为可以将西洋政治哲学史上的诸“约”论(包括“神约”“政约”与“社约”在内)皆称为“单约论”。这里所说的西约之“单”是与墨约之“通”相对而言的,不仅是指西约立约主体的日趋单一性特征,亦指其并非重视关系而是看重主体的单向度性作用。这样看来,与墨约相比,西约并不能在治国理政中真正全面而有效地从宏观整体及微观局部把握国家治理格局,为当代中华治国理政提供系统实际的“约”论基础,这也是西约在历史上反复走向绝境而又须另辟蹊径以摆脱困境,之后又再入窘境的怪圈现象频发的重要原因。
可见,中华若纯粹以西化视角推广西洋单约论思想,这本身就潜藏着堕入怪圈而不能自拔的隐患。欲从中摆脱,惟借助中华墨家通约论方可寻得出路。所以,西洋单约论虽然在其自身历史演进过程中不断进行着内部超越,却从未能够真正超越2400年前由中华先秦墨家所提出的通约论。这是值得研究国家治理问题及中西国家治理模式比较的学者所反思的。
从这一点而言,我们可以毫不讳言地表示,先秦墨家的互系性通约论较之西洋单一且单向性的单约论而言可谓是“大约论”。之所以曰“大”,在于通约论充分实现了以“天”、“君”、“民”为代表礼治(德治),人治与法治三款国家治理模式在中华大地的良性互动,其视野之宏大、立论之眼深,非“大”无以冠之。
相比“大约论”,西约则主要偏执于发展法治这种国家治理模式,而人治固然也存在于西约立论中,却并非近现代民主国家治理模式之主流,同时礼治(德治)则诉诸于与“政”相分离之“教”。因此事实上,西约不仅重点偏执于发展法治这一款国家治理模式,而且亦没有很好地将其余的礼治(德治)与人治同法治三者实现良性互动,这也是西约须向墨约借鉴与完善之处。所以,我们当然不妨称西为“小约论”
墨约之所以称“大”,还有第二个原因,即它亦是中华古代传统治理模式之普遍“约”论基础的典型代表,中华古代传统所曾出现过的治理模式正是以这种互系性通约论为基础而构建起来的。有学者这样描述过中华古代传统治理模式之本质:
君责臣民以本分,民责君臣以本分,夹在君和民之间的百官,在恳请君尽到本分的同时,又责民众以本分,这在传统政治文化中是一种极其常见的现象。而夫妇、父子、兄弟、朋友、亲戚、邻里长幼之间,也无不在“躬自厚”的同时热衷于“责于人”,尊卑有序中又透出相互制约的一面。
这恰恰体现出了建立在互系性通约论基础之上的“天”、“君”、“民”三极所具有的互系性相约之特征:“躬自厚”就是上位之“君”与下位之“民”共约“天”,进而发展出礼治(德治)的治理模式;“责于人”便是“君”约“民”及“民”约“君”的交互表现,进而发展出人洽与法治的治理模式。而这样一种存在于中华古代政治传统中的互系性通约论基础,对于当代中华治国理政事实上亦有重要的参鉴及启示:
这种政治文化在设计者的理念中是服务于实现社会和谐的总体目标的。因为,和谐有赖于社会成员自觉地各安其位,各尽其职,或者说有赖于人人恪守本分。
选择何种“约”论基础,便是为选择何种治国理政模式提供了强有力的理论前提。因此,当代中华十分需要重新反思纯粹西化的主张运用西洋单约论作为当代中华治国理政模式的理论基础与中华文明的本身承续是否兼容的问题,亦要考虑舍中华“大约论”而用西洋“小约论”及其纯粹的宪政治理模式的这一做法是否真正值得且可行。同时,当代中华还须真正挖掘并汲取中华传统文化中能为其治国理政提供当代积极价值的思想资源,为当代中华治国理政做好文化与理论支撑。
在著者看来,中华先秦墨家通约论对于当代中华治国理政极具价值。当然,墨家在阐述其互系性通约论之具体应用等方面在今天看来或许略显狭隘且亟待完善,应当赋予其新的当代内容。但不可否认的一点是,若刨去这些具体应用层面的局限性不论,墨约在学理上得出的“天”、“君”、“民”三极互系性通约论及由此发展出的礼治(德治)、人治与法治三款治国理政模式的理念的确能为当代中华治国理政予以丰富的启示。
一个国家的治国理政,特别是当代中华的治国理政,既要重视法治,亦不可偏废礼治(德治)及人治的作用。也就是说,我们在通过批判吸收西洋法治治理及中华古代传统法治文明来建设法治中国以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此乃“法治”)的同时,亦需要中央与地方各级执政者从人民群众中汲取力量,发挥自身的先进性及纯洁性的领导水平(此乃“人治”),并在此基础上凝聚起执政者与人民的道德支撑,树立、弘扬、培育并践行和谐中华的道德伦理价值观(此乃“礼治/德治”)。在这些方面,说秦墨家“天”、“君”、“民”三极互系性通约论具有跨时空的当代价值是毫不过分的。
声明:该文观点仅代表作者本人,国学百科网系信息发布平台,仅提供信息存储空间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