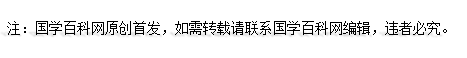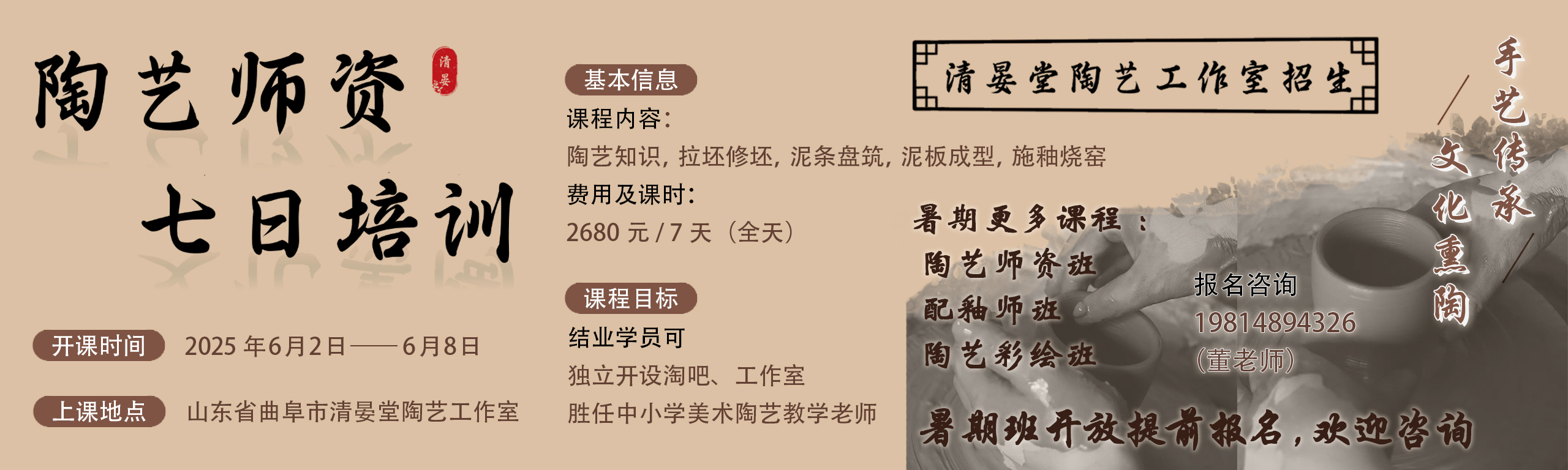作者:建安章武
记得读过这样一首诗,诗名直白了当,《过陈琳墓》。
过眼满满的都是歆慕尊崇,只不知温庭筠是否想过,他所仰慕的以文章名世的陈琳陈孔璋,其实也与他本人一样一生飘流蓬转,一样的不得其时。
陈琳字孔璋,广陵射阳人,“建安七子”之一,曾入何进袁绍幕府,后任司空军师祭酒,徙丞相门下督,作品多散佚,存者以《檄豫州文》《饮马长城窟行》最为知名,有言“曾于青史见遗文”,多指此两篇。

广陵,射阳,应在扬州,他是建安七子中唯一的南方人。
也称得上是游宦在外了。
他应当是那个兵荒马乱的年代里南方士人中少有的真正到过北方的人,“长城”一诗颇具民歌风范,情真可感,当不是闲思之作,也正可知他平生之志。
他也许同样想过为天下做点什么。
只是,这簇飘蓬想要在异地他乡扎稳根系,在汉末特殊的政治环境下实在困难。他对世俗功业的主观追求远胜于同时期诸多文人,以至于臧洪说他“饶利于境外”。不争则无立锥之地,争则不免为士林所讥,真正两难。地域与观念两大分歧,造就了陈琳游走于团体边缘的尴尬处境。
这种境况,不见于本传记载,但在其他人的生平记述中,有时可以窥见一二。
《吴书》中记载:“(紘)为作赋,陈琳在北见之,以示人曰:‘此吾乡里张子纲所作也’”每读至此都觉得可怜可爱之至,就像童蒙小儿向人炫耀自家兄姐的好处,恨不得昭告四邻八舍。他答复张紘时也说“此间率少于文章,易为雄伯”其实哪里是少于文章,分明是被北方群体挤到边角里的无奈自嘲。
正像他所说的,他也是有足以自傲的成绩,不独诗赋,仅檄文一篇,便被《三国志》全篇引用,其篇幅甚至长于部分传记全篇,也足见时人对其的高度评价。后人称其“文誉已三朝”,岂止三朝,分明已历千载。

只是这殊荣绝非他本意!他毕竟经历过建安之前那段风起云涌英雄草创的时代,对那份建功立业的豪情更加感同身受,他绝不会甘心只做个词客文人!力谏何进的他,传书臧洪的他,执着“立德垂功名”的他,仰慕“非常之功”的他,又怎么会甘于平庸,沉沦众庶呢?!
但又能怎么样?文章立身,本便易为流俗所轻。上官要的是文章,是写的出文章的笔,只要文章合意,那执笔的人究竟是哪一个,原本也无所谓。任你才比相如、子云,最终也逃不过被工具化的命运。
“与天下隔”,他被困在河北了。理政能力需要实证,可他连向后人证明自己的机会都没获得。
若真能见证红日东回扶桑也便罢了,可惜到了最后,山风萧萧、路阴天暗,“建安”终究不过是一个落空的期许,一个悲壮的幻象。
也许根本没到最后,在他说出“箭在弦上”那句救了他一命的妙语时,那个“鹰扬于河朔”的广陵志士就已经睡去了,留下的只是风中摆荡的蓬草,蒙着一层灰蒙蒙惨淡的光。
能说什么呢?姑且归结于不可知的命运吧。
于是哪怕是白玉沉渊时如烟花般喷涌出的最后一点鲜艳炽热滚烫的血溅到眼前,也不过只能激起心底一点小小的波纹,涕泪沾襟而已。
反正已几近是一副空壳,既然留不下,就便舍弃了也罢。
于是,建安二十二年,一切喧闹欢愉悲叹低吟都仿佛戛然而止,只留下狂风撕扯白幡的响。
乡土远在天边,墓址至今不明。臧子源言“生死而无闻”,竟险些言中。
高树多风,海水扬波,时间会掩埋住曾经鲜活的一切,诸多文辞章句早与七尺之躯共为一抔黄土,无数的无数早已都散佚在高风与海涛中,纵然是留下的人利剑在掌,又有何用?惟叹息而已。
只是总令后人想望不已。

倘若词客有灵,应当仍旧是着笔千古檄文时的壮年风貌,把笔临风气俊神雄,文锋所向意势横绝,仿佛无论眼前的道路通向何处,只要张开双臂便能包吞。文人词客最为人所熟知的,怕都是他们最风华昂扬的时候,连随手写下的只言片语,叫后人读来都觉得字字生光,笔笔都有生气。
孔璋行矣,不知如今的骊歌,在遥远的建安二十二年可否听闻?
只恨时迁岁晚,想几千年来临风倍惆怅的,绝不独温飞卿一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