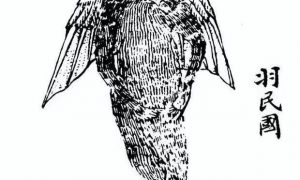作者:钱 爽 张耀南
那么在墨子看来。何者才能立为“法”(“然则奚以为治法而可?”)?墨子并未先直接表明何者可立为“法”,而是先强调了不可立为“法” 者有何。他认为,立人以为天下从事之“法”是万万不可的,并着重点明“父母”、“学”、“君”这三类人尤其不可立为天下从事之“法”(“故父母、学、君三者,莫可以为治法”)。究其原因,便在于这三类人天下虽众,然而其中“仁者寡”,若以众之不仁者为“法”,则是“法不仁”。而在墨子看来,“法不仁”是绝对不允许出现的(“法不仁不可以为法”)。所以,天下之为“父母”、为“学”、为“君”者虽多,但其中的不仁者众而仁者寡,自然立人(尤其是立“父母”、“学”与“君”这三类人)以为天下从事之“法”是绝对行不通的。
墨子在阐述不可以不仁之人为“法”的观点时并未像西洋近世社会契约论者那样是建立在某种逻辑性的人性预设基础之上的,这种逻辑性的人性预设只存在于逻辑假定层面而现实中并非完全实然存在的人性。墨子则是立足于现实经验确然的情形)人有仁者与不仁者之分,而仁者寡于不仁者。因此在墨子看来,若以人为“法”其实并不可靠,因为人(尤其是“父母”、“学”与“君”这三类人)并非完全是仁的或者能够永远保持仁的状态。墨子的这一前提并非同西洋近世社会契约论者那样是一个预设的逻辑性前提,实际上是一个现实性前提。在这种现实性前提的基础上构建起来的“法仪”篇的理论是一种常态理论而非西洋近世社会契约论那种特例理论,因为逻辑性前提只可能存在于构想中,与现实极有可能不符甚至背离、脱节。
墨子心目中所认可的可立为“法”者便是“天”(“莫若法天”)。为何立“天”为“法”?这是因为“天”本身具有最广大的公共性与统一性特征:
天之行广而无私,其施厚而不德,其明久而不衰。(《墨子·法仪》)
所以在先秦墨家互系性通约论的“法”“君”“民”三极中,“法”即是“天”,故“法”可用“天”替代。这样一来,墨家互系性通约论之三极又可表述为“天”“君”“民”。“天”所具有的这种最广大的公共性与统一性特征,使得“天”可约(或采用前文中的“若”字亦可)“君”,或者说“君”受“天”所约:
圣王法之。(《墨子·法仪》)
同时,“民”亦受“天”所约:人无长有贵贱,皆天之臣也。(《墨子·法仪》)
由此,“君”与“民”虽然一个居于治国理政体系的上位,一个居于治国理政体系的下位,但在作为天下从事之“法”的“天”面前,“君”与“民”二者都处于“天下”这样一个相同的层面,故二者皆平等地受“天”所约,而不会因“君”居上位便比居下位之“民”受“天”所约要少:
既以天为法,动作有为,必度于天。天之所欲则为之,天所不欲则止。(《墨子·法仪》)
若再详而言之,“君”与“民”受“天”所约的具体表现有:
恶人贼人者,天必祸之。曰,杀不辜者,得不祥焉。(《墨子·法仪》)
可见,在“天”面前,同处于“天下”层面的“君”与“民”若“以别故,乖乎性道之常”,则“天”必约之以“祸”(或“不祥”),以此而约“君”与“民”不得为恶。“法仪”篇中便引暴王桀纣幽厉为例以明“君”与“民”受“天”所约之理:
暴王桀纣幽厉兼恶天下之百姓,率以诟天侮鬼,其贼人多,故天祸之,使遂失其国家,身死为僇于天下,后世子孙毁之,至今不息。(《墨子·法仪》)
但是,“天”并不因其可约“君”与“民”便成为至尊至高之一极。因为墨家通约论三极是彼此互系的,所以“君”与“民”在受“天”所约之同时,亦可约“天”。具体表现在:
爱人利人者,天必福之。(《墨子·法仪》)
换言之,“天”可以通过“祸”或“不祥”以约“君”与“民”勿作恶;同时“人”亦可以通过“兼而爱”或“兼而利”之行动“敬事天”“以兼故,通乎物之所造”,从而约“天”以赐福,而不再降祸于“君”与“民”,以使天下之君民“兼而有之”“兼而食之”。“法仪”篇中亦引禹汤文武为例以明“君”与“民”约“天”之理:
昔之圣王禹汤文武,兼爱天下之百姓,率以尊天事鬼,其利人多,故天福之,使立为天子,天下诸侯皆宾事之。(《墨子·法仪》)
综上,“法仪”篇实辄是《墨经》通约论中“君”“民”与“天”共约这一学理之具体应用。在具体应用中,“君”“民”与“天”存在互系之约,这种互系之约是双向而非单向的:
爱人利人以得福者有矣,恶人贼人以得祸者亦有矣。(《墨子·法仪》)
“君”“民”与“天”在互系性通约论中没有一方可永远居于至尊至高之上位,彼此交互而约,这才是《墨子》一书“法仪”篇中“君”“民”共约“法”,也即“君”“民”与“天”共约之真谛-治法天。
(二)“七息”篇:“君”约“民”之应用发微
有关《墨子》一书“七患”篇之主旨是何,多数治墨学者皆认为是针对“君”(即治国者)而提出的节用之道。但著者认为这种解释并不妥当,“七患”篇所针对之对象并非只是居于上位的治国者“君”,实际上是以“君”之视角约“民”(或曰“臣民”)的具体应用。倘若如此,则“七患”篇亦非只是提出了节用之道,以著者观之该篇所讨论的内容实辄是“君”以“防患”与“备国”而约“民”。基于此,著者发现在诸治墨学者中,唯张纯一先生对“七患”篇之主旨的见地及把握与著者不谋而合。张氏有云:“此篇不尽属节用之余义,亦教人严密为备,防患于未然也。”张氏还具体云:“此篇冡法仪而次之,明人不法天兼爱,所染必不当,则修身无方,亲士无准,而七患至矣。盖教人严密为备,防患未然,期与天地同常也。”
声明:该文观点仅代表作者本人,国学百科网系信息发布平台,仅提供信息存储空间服务。